人,生来即是父母的孩子,“名”一般为父母亲人所赐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家族当世当时的眼界和心界、人生观和期望值。
“名”中有伯、仲、叔、季或按照其他族谱辈分的,现在也一直延续。史书中功高勋盛的大臣,还存在皇帝也不直称其名的现象,说明于人的任何其他称呼而言,“名”最重。所以,郑重场合直呼其“名”或为不雅,甚有蔑视之嫌。不过,自己说自己的“名”,则可视为自谦。另,因为避讳皇室或尊长而后来改名者,也大有人在。而对于无字号者只能呼其名,是因为没得选。此外,还可根据是否省略姓氏,判断二者亲疏程度。
“字”是二十而冠后,族长或有威望的老者所赐,讲究的家族会办个仪式,称为冠礼。如其叔叔、阿姨、伯伯、师父等长辈,或同辈交好,可改称其“字”。有“字”青年,证明其已然成人,可以并需要为以后的行为负责,此为知荣辱的成长仪式。如李阳冰,字少温;颜真卿,字清臣;杜甫,字子美等——这些“字”,多数是其“名”的表注、引申或反向互补之意。也有不少书法家以“字”行,如孙过庭,“名”虔礼,过庭实则是他的“字”。
说到“号”,常规粗略统计,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。一是其姓氏加上出生地地名,这种称呼相当于现在的家乡名人的意思,如赵吴兴,董华亭等,宋朝被称为“天水之朝”,也是这个意思。但对于村、镇、县、乡等小的行政区划,往往囊括的地域相对大一些,如高邮人秦观,别号淮海居士,淮海地域比高邮市三垛镇少游村大得多,且为《尚书·禹贡》中古地名,目的多为照顾当事人出身体面和“包装感”。二是代表当事人长时间宦游或者一生中相对有成就的地方,再或者是受封地,如徐会稽、颜平原、颜鲁公、朱考亭等。三是其官职称谓,如南书房行走一类,再如徐少师、杨少师、李西台、张长史、祝京兆等。四是与其工作过的部门职位有关,古代不乏有些是“戴高帽”的过誉,如米南宫,他在南宫职位并不算高。五是尊号或谥号,如宣圣、和圣、欧阳文忠、赵文敏、董文敏等。六是先自己或敬重的尊者题个斋号,然后书斋里的人自称或被称作某某室、某某斋主人的情况,直到现在于书画圈也很常见。
还有很多“号”为自取或他取,如归来子、陶隐居、云林子、云谷老人、白石道人、严夫民伯、松雪道人、水精宫道人、香光居士、黄山山中人。实则自取的“号”多一些,这类“号”多表示书家对佛、儒、道、杂、兵、农、法以及宇宙天地自然等,某种纯粹或几种混合价值观的彰显,即拥有某自取的“号”者,是某种价值取向的倾注和代表。另外,不同时间段用不同号的人,在某个时间段,可相对直观地映射出书法家本人的阶段性价值取向,这也对研究书法家理论和创作的学术主张和风格演变,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
再者,书法家中一人会有很多的“号”。此类人相对“多变” ,有一种“去年的衣服配不上现在的自己的气质”的感觉,也常常能反映出其在该行业中不断探索和调整的轨迹。另外,很多书法家学人会共用一个号,反映其在某个时间段,与前人精神的相通点和效仿性,或可简单理解为那时的偶像或心慕手追、“相爱相杀”一类,如董文敏与赵文敏。
古人“字”“号”能有很多个,那么文献中不断转变同一个人的称谓,实乃常见。一般意义上,前人私家著述提及古人,多用其“字”“号”、官职、地望、谥号等,原因有三:一是为了尊重,二是炫博,三是行文避免重复。也有著作中目录的题例直接书写书法家姓名,具体章节与行文中会使用多种称呼的,如马宗霍的《书林澡鉴》《书林记事》等,因为这类总结性的书论著作,必然会有引用归纳前人研究,所以是为记录传抄和承袭。此外,还有尽可能全力以“字”“号”行文者,如《画禅室随笔》以及董其昌的诸多按评题跋。所以,文献中提到“黄庭坚”,有时写作涪翁、黔安居士、黄太史等。
还有的称呼,与书法家本身的“名、字、号”无直接关系,如长公、次公、少公等。当然,并不是所有名字中带“长、次、少”都是因为长幼排序,并且即便称为“长”的,也有非常规用法,如苏轼本是苏洵第二子,轼兄早夭,后人称苏轼为苏长公,以表秩序和尊长。还有像在朱长文《墨池编》目录里的记录,历代书法家都是直书其“名”,而在罗列他自己写的《续书断》时,署名却是他自取的“号”——灊溪隐夫。
虽然用书法家的“字”和“号”表尊重,但现在的正规学术著作却也还是多直接用前贤的“名”,原因如下:著书和行文的原则是简捷客观,古人“字”“号”容易混乱,史上有“文忠”一堆、“云林子”若干。“黄门令”有可能说的是史游,有可能是他人,还要根据设置文字的不同时代节点和从事领域自行判断。直接用“名”,毕竟可以省去不少麻烦,也更清晰,所以,在这类意义上,针对直接用“名”,而归纳为对古人不敬不免狭隘。
在口头语言中,有“字”“号”者,长辈、平辈都可以直呼。对晚辈或后人而言,有官职的叫官职,有辈分的可根据辈分叫伯、叔之类。书面语言提及某人可称呼“字”“号”,长辈、平辈、甚至晚辈后人都可写入文中。所以,该小文研究范畴为归纳文献中的习惯用法,因为口头语更复杂,几乎口头说不清。另外,文中所举书法家例子,多来自隋唐五代、宋元明清相对往后的历史时期,再往上追溯,单单古人的姓、氏,如孔、姬、周、嬴等也异常复杂,要理清也是小切入点的大学问,所以,此处研究范围只得一再缩小并往简化方向梳理。
关于书家“名、字、号”这一小的研究点,从文明传承的客观角度来看,书法文献的认知断层,或可找到一个很基础却又很有效的突破点,否则,多数古文献所记录,让人不知所云。古文献中还常出现研究同一个人却让人以为是多个人,又存在同一文中出现多个称谓却不知所说为同一个人,如《山谷自论》中提到的“苏才翁子美”,言何人,言几人,如何断句?诸如此类随眼所见问题,虽基础却也容易被人质疑所做学问的可靠性。
再者,研究古人名之外的“字”与“号”,还可提供一种思路,如早些年讨论当代书法还有无“南北书派”区别话题时,对古今书法家出生、生活地域也期待有个相对清晰的梳理。地域、名、字、号、考上进士的年龄,考完授予的编撰还是编修,以及官职的具体工作事务、升迁史等,虽然都不是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决定一切的要害,却如血液毛发般,有过对人之容貌与性情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(闫敏歆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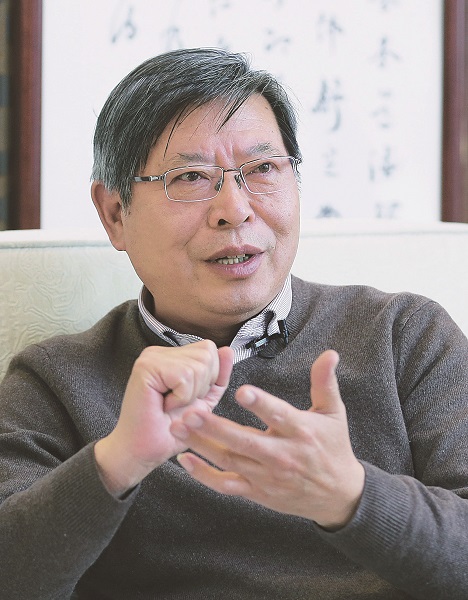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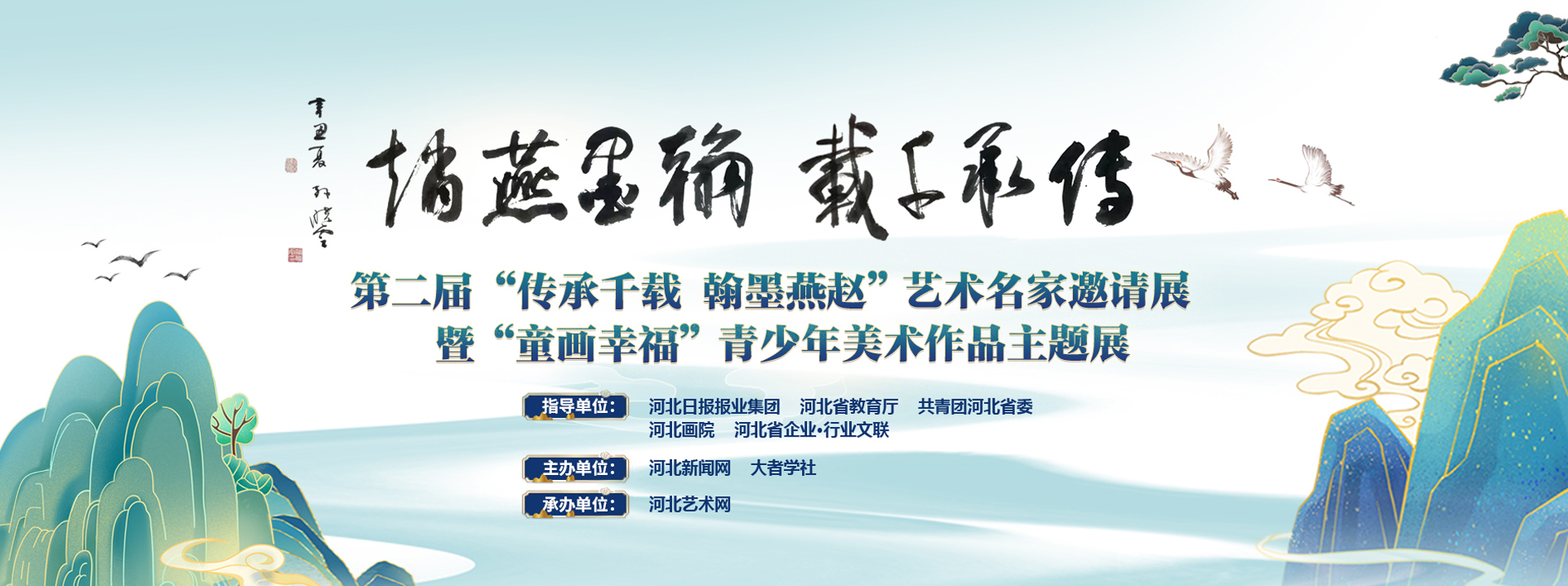

 冀公网安备 13010802000999号 | 冀B2-20100322
冀公网安备 13010802000999号 | 冀B2-201003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