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嘉伊始,碑学兴盛而帖学式微,划时代级的书法家都在“碑派”阵营当中,崇尚碑学的书法家不断涌现,在这百年之间,碑学似乎成为了时代的主流。但同时,碑学始终难以获得统治者的推崇和认可,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碑学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播和渗透。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遗存书迹来看,可发现碑学确实有相当的影响,但针对不同类型的墨迹,这种影响表现的显然不尽相同。
一般认为,以有无金石气(即能够表现金石苍茫雄浑的气息)作为“碑学书法”别于“帖学书法”的特征。从范围来看,碑学书法主要包括了先秦至秦汉的钟鼎铭文及碑刻和南北朝碑刻,因此还应包括篆隶书的用笔和字形特征,以及魏碑“斜划紧结”和体态宽博等特点。而帖学书法则是“研美流便”的“二王”一脉风格,一般将魏晋至明末的书法归为帖学(当然不绝对,其中也有不少师法秦篆汉隶的书法家)。以此标准,再来衡量此期的墨迹(这种标准只具有相对意义):
首先,从故宫博物院“丹宸永固”展中出现的部分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(20世纪20年代)工作手记中可以看到,民国初年,规范的工作行文几乎都是风格秀雅的传统帖学书法,少见碑学痕迹。可见,在相对正式的公务行文中,帖学仍是主流的书风,即便其中参入一些碑学的风格特征,也多体现于个别字的用笔、体态之上,总体上仍呈现为帖学的面貌,这也反映了时至民国,官方的书样仍是以帖学为主流的。
再看民国时期的文人手札。笔者从北京中国书店、古玩市场、友人私藏中收集到一些无名的文人手札,书体多为行草书,从风格来看,大部分仍然处于帖学的范围之内,帖学的用笔、字形特征还是清晰可见,也有部分具有一些圆厚朴实的用笔和北碑“斜划紧结”的体势特征,总体看,帖学风格的墨迹明显较多。与此同时还应关注到其中部分手札法度稍弱,透出一股自由烂漫的气息,这些书迹可能难以简单地归为“碑”或“帖”,或者断定二者比重,但也侧面说明碑帖之间似乎并不存有清晰的界限或本质的差别,两者的融合应是一种必然结果。
再看名人书迹,以《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》为例,其中收录358位名人书翰,多为晚清到民国的作品,书体为楷、行、草三体(行书偏多),间杂几幅隶书作品,上至明代沈周下至近代梅兰芳、徐悲鸿、张大千等人。这些名人的尺牍、信札都是以文人交流、记事为目的而产生的,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书法家的日常书写状况。根据这些名人书翰,可以注意到几个方面的特点:其一,大致为18世纪以前出生的书法家的书翰,几乎不见碑学的痕迹,仅见金农一纸书翰有明显的碑学风格;其二,从邓石如到19世纪50年代前出生的书法家的书翰,笔画圆厚的作品开始增多,一些作品中帖学的法度有解散的趋势,但总体看,纯粹的帖学作品仍然是多数,较为明显的碑学作品只是少数,部分有碑学渗入的作品中,帖学的风格特征仍为主要,即便如晚清甚为推崇碑学的几位书法家,如阮元、包世臣等,其书翰中呈现的风格,更多的也仅是在笔画线条上表现得厚重质朴一些,用笔、字形和整体的气息,仍然是较为明显的帖学风格;其三,19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书法家的书翰,开始出现碑帖交融的现象,如郑孝胥、曾熙等人的作品中,已表现出较为均衡的“碑帖相参”现象。从数量上看,《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》中帖学风格的作品明显占据多数。
从以上三类作品的比较中,可以得出一个结论:帖学在18世纪至20世纪前期里,仍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,而碑学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以审美、赏玩为目的的书法作品中,而以记录、流通为目的的书法作品则多呈现出“帖派”的风貌,并且从数量来看,显然后者更占优势。
而帖学在碑学兴盛的时期内,仍能保有这种具有优势的影响力,毫无疑问首先应归功于科举制的影响。科举制在清代虽在某种程度上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,但不可否认时至清代科举已是一项高度成熟的选举制度,其社会影响力是空前的。康乾盛世使得人口迅速增长,尤其在乾隆年间,出现了爆发性增长。人口激增的同时,相应的参与科考的人数也不断上涨。
由“随着清代人口持续上升,即使经过岁科两试筛选,各县有资格参与乡试者也不下千人”“清代共开112科,取进士16849人,平均每场录取进士约为240人。但这一数字与庞大的应试者数量相比,还是十分稀少的”等记载可见清代参与科举考试的人口数量之庞大,而这种极高的参与度和传播性,与科举制度本身对知识阶层影响的深刻性是分不开的。即便如康有为这样的碑学书法家,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也专列“干禄书”一章,可见科举考试之影响。在“以书取士”的制度下,“馆阁体”风靡一时,科举制的影响越大、传播力越广,“馆阁体”的使用效率也就越高。“颜面赵底”“欧底赵面”的风格无疑都隶属帖学的范围,在其盛行扩大的同时,也自然地使帖学书法的影响力得到延续和提升,科举制也在不经意中成为了晚清帖学书法最大的“传播动力”。
在清代书法教育中,书法范本也多是围绕晋唐法帖来选择,杨宾在《大瓢偶笔》中记清代书法启蒙教育的范本选择时言:“法帖以逸少黄庭、东方赞、圣教序、乐毅论为主,而附之以子敬十三行,伯施庙堂碑、破邪论序,信本化度寺、邕禅师塔铭,虞恭公小字墓志铭、九成宫醴泉铭、定武兰亭,登善颍上兰亭、黄庭、孟法师碑、枯树赋、阴符经、度人经,再观澄清堂、淳化阁、绛帖、戏鱼堂、太清楼诸帖,以尽其变。”以及根据《清史稿》对国子监的记载,其监生需“日摹晋、唐名帖数百字”。可见,清人学书的启蒙阶段是以帖学为本的,尤其冀望以晋唐楷书中正严谨的法度为初学者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除了官学,民间教育也同样如此。清代统治者为了提升对教育的管控,进一步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,将民间的私学教育纳入到官学的管理中,朝廷对于民间办学也多予以支持和奖掖。当然支持鼓励的背后是以民间私学成为了科举的附庸为代价的,“读书应举”已是民间书院的核心目标。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在《变通书院章程折》中奏道:“查近日书院之弊,或空谈讲学,或溺志词章,既皆无裨实用,其下者专摹帖括,注意膏奖,志趣卑陋。”《中国书院制度》中也有记载:“雍正而后,主之者已不复讲学,教者失其所以为教,学者失其所以为学,有心人惄焉忧之,语其通病……朱子有言,科举不累人,人自累科举耳。夫书院非犹是也哉。”官方意志的介入下,官学的书法教育体系也自然而然地贯彻到民间教育中,读书人还必须要勤练“馆阁书法”,才有机会考取功名,这样帖学在民间的影响也就进一步深化了。
除了上述原因,从书体上看,帖学和碑学由于书体演变的原因,其交集一般认为是楷书,这也使得不同书体中二者影响必然会有不同。再从功用上看,“二王”帖学传承千余年,多是用于尺牍信札之间,形成了快捷实用的书写性特征。而碑派书法为求表现“金石气”,一些书法家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书写的舒适性或便捷性,如何绍基就用“回腕法”写字,数字之后便显疲态,正所谓“短笺长卷,意态挥洒,则帖擅其长”。
综上所言,由于帖学自身的特点、人口的激增,以及制度、教育的需求等原因,使得清代帖学虽没有取得较高的成就,整体也相对缺乏活力,但其影响力并没有因此受到较大的冲击,相反在日常交流、记事一类的书写中,仍然表现出较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。(侯愚堃)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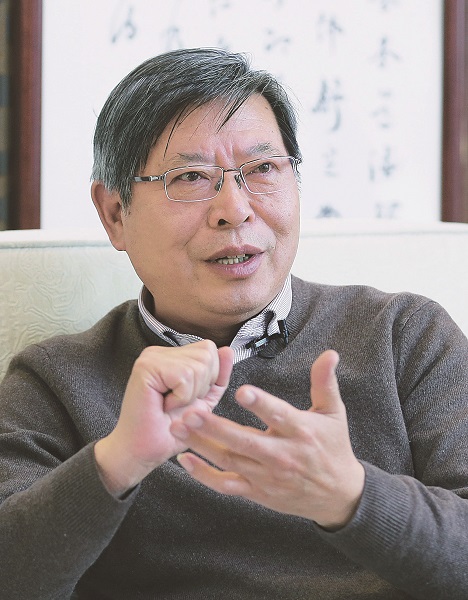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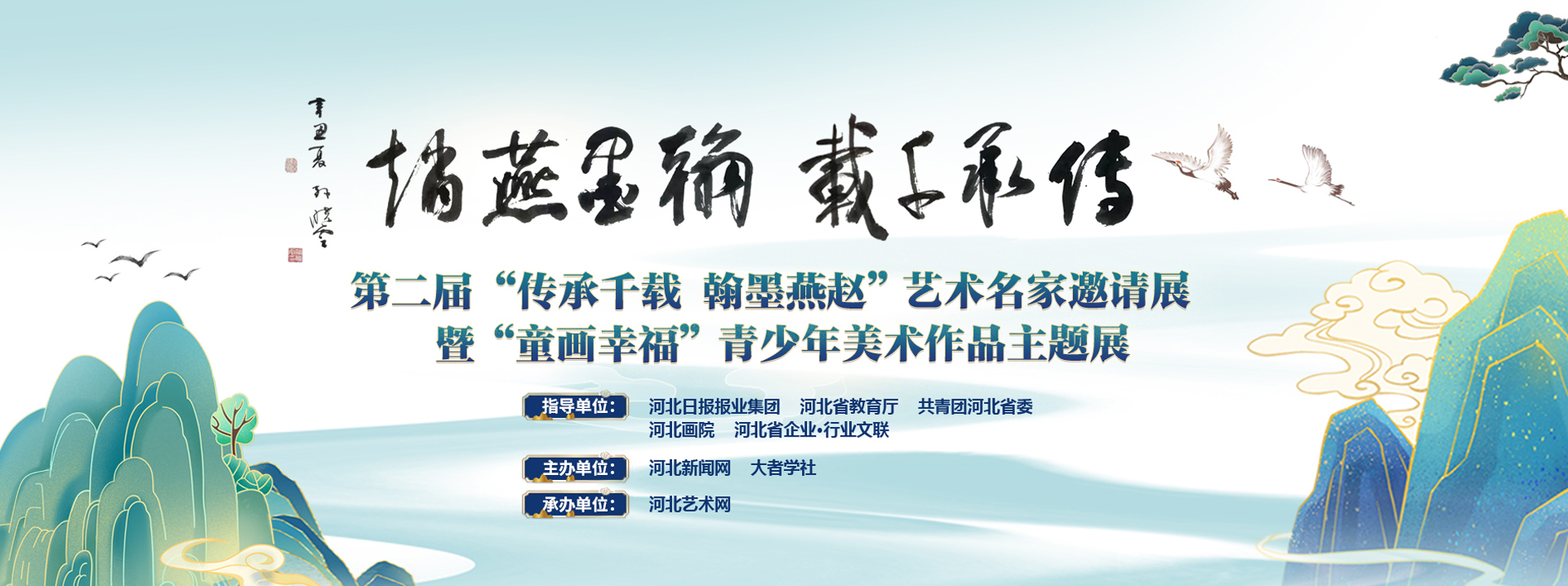

 冀公网安备 13010802000999号 | 冀B2-20100322
冀公网安备 13010802000999号 | 冀B2-20100322